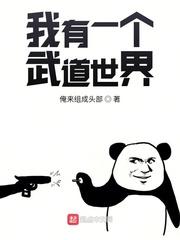明治文学之追忆(第2页)
在这幽默中间实在多是文化批评,比一般文人论客所说往往要更为公正而且深刻。
这是我对于户川最为佩服的地方,我在以前佩服内田鲁庵的论文也是同一理由,因为他们的思想都是唯理的,而博识与妙文则居其次焉。
唯理思想有时候不为世间所珍重,唯在渐近老年的人自引起共感,若少年血气方盛,不见赞同,固亦无妨也。
其次还有这样的两位,他们本来或者并不是一路,但在我觉得同样的爱重,所以唐突的拉在一起来说,这便是永井荷风与谷崎润一郎。
永井的小说如《祝杯》等大都登在《中央公论》上,谷崎的如《刺青》等是在《新思潮》上发表的,当时也读过,不过这里要说的乃是他们的随笔散文,并不是小说。
老实说,我是不大爱小说的,或者因为是不懂所以不爱,也未可知。
我读小说大抵是当作文章去看,所以有些不大像小说的,随笔风的小说,我倒颇觉得有意思,其有结构有波澜的,仿佛是依照着美国板的小说作法而做出来的东西,反有点不耐烦看,似乎是安排下好的西洋景来等我们去做呆鸟,看了欢喜得出神。
废名在私信中有过这样的几句话,我想也有点道理:
“我从前写小说,现在则不喜欢写小说,因为小说一方面也要真实,—真实乃亲切,一方面又要结构,结构便近于一个骗局,在这些上面费了心思,文章乃更难得亲切了。”
我对于一般小说不怎么喜欢,但如永井晚近所作的《东绮谭》,谷崎的《武州公秘话》,所写的方面不同,我读过都感觉有兴趣,不过他们又还写有散文随笔,那么我所喜欢的自然还是在这一边了。
永井的《日和下驮》—这书名翻译不好,只好且用原文,大概还是最初登在《三田文学》上,后来单行,是我的爱读书之一,文章与意思固然都极好,我的对于明治的东京的留恋或者也是一种原因,使我特别爱好这一册小书。
此外的《荷风随笔》,《冬之蝇》,《面影》,以及从前的《杂稿》都曾收集,惜已有散失,《下谷丛话》是鸥外式的新体传记,至今还在看。
谷崎的随笔大概多是近几年中所写,我所喜的是《青春物语》以后的,如《摄阳随笔》,《倚松庵随笔》,《鹑鹬陇杂纂》等均是,《文章读本》虽然似乎是通俗的书,我读了也很佩服。
这两位作家的辈分与事业不是一样,我却是一样的看重,关于文章我们外国人不好多嘴,在思想上总是有一种超俗的地方,这是我觉得最为可喜的。
讲到末了还有一位岛崎藤村先生。
他在日本新文学上的位置是极其重要的,拿别人来和他作比较,例如夏目与森这两位,一是大学教授,一是军医总监,文学活动时期只以明治大正为限,藤村则一生只是弄文学,从二十六岁时发表新诗集起,后来做小说,至七十二岁逝世,还在写《东方之门》未曾完了,前后将五十年,自明治以至昭和,一直为文坛的重镇。
他的诗与小说以前也曾读过好些,但是近来却爱看杂文,所记得的还是以感想随笔为多,在这里我也最觉得能看出老哲人的面影,是很愉快的事。
我不能正当的称扬其诗与小说的功绩,只在讲到随笔的地方说及他,便是为了这个缘故。
藤村随笔里的思想并不能看出有什么超俗的地方,却是那么和平敦厚,而又清澈明净,脱离庸俗而不显出新异,正如古人所说,读了令人忘倦。
大抵超俗的文章容易有时间性,因为有刺激性,难得很持久,有如饮酒及茶,若是上边所说的那种作品则如饮泉水,又或是糖与盐,乃是滋养性的也。
这类文章我平常最所钦慕,勉强称之曰冲淡,自己不能写,只想多找来读,却是也不易多得,浅陋所见,唯在兼好法师与芭蕉,现代则藤村集中,乃能得之耳。
关于白桦派的诸君,今且从略,其理由则是已在明治以后,不在此文所说范围之内,其次亦因我与诸君多曾相识,故暂且谨慎也。
鄙人本非文人,岂敢对于外国文学妄有论列,唯因杂览日本著作,颇受裨益,乃凭主观稍加纪录,以志不忘,见识谬误自不能免,但如陶渊明言,愿识者见而恕之而已。
民国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