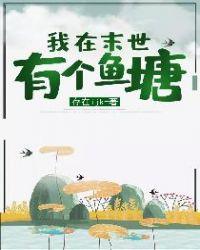我为美食狂
我为美食狂叶秋叶本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厨师,却因为一个小小的误会得到了一辆美食基地车,从此踏上了以美食征服世界之旅。被誉为全球最大老饕的米其林美食杂志总编伊莎贝莉在杂志上公开向叶秋叶求爱,声称叶...
仙途遗祸
水馨穿越修仙界,以天才的资质踏上修仙路,举目四顾前无各类奇葩主角需要逆袭后无各类脑残极品欢快蹦跶左有好友若干右有蓝颜数位水馨喜忧参半这世界的节操掉得凶猛,智商居然还不曾欠费...
国家让我去当猫
...
我在末世有个鱼塘
末日里,他们都叫我神农,我有些名气,爷爷给我留下一座山和一片鱼塘作为遗产,我在后山的血尸地里养血尸卖血灵芝,把血尸当做饲料在鱼塘养鲨鱼。我赚的盆满钵满不愁吃喝。但是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没有人知道,...
中医:回到知青下乡那些年
作为一个城市里的小中医,一觉醒来,回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正赶上恢复高考,知青回城,土地承包那年,乘着时代的东风,有人下海经商,成了万元户。有人埋头苦读,成了大学生。王承舟却在小乡村里当起了赤脚医生,凭借一手精湛的医术,购置起三大件,找了个小对象,开了间草药铺。闲了上山打猎,馋了下河摸鱼,日子平淡而快乐。在邻里...
混在大唐做驸马
建个群,全订粉丝群131341657来时无迹去无踪,大唐贞观寄此身。漫随贫富皆欢乐,混作长安一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