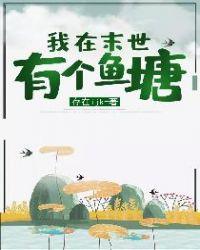农家俏媳妇:养夫带娃种田忙
袁隆平团队的农业专科女博士,一朝穿越,成了软弱可欺的小村姑,还有个小包子瞪着水汪汪的眼睛喊娘亲,没粮没钱,吃了上顿没下顿不说,前有极品亲戚欺压,后有伪善闺蜜陷害,温婉表示不怕不怕,撸起袖管儿,赚钱养...
农女手里有口泉
...
八零军嫂上位记
重生的姚瑞雪依旧成了某人的血库,如此,她决定在孙家踩她血上位之前,抢先抱住大腿不被其用,好以报仇虐渣,却不想大腿太粗,不如攻其心直上位。某团长,抱什么大腿,快到我怀里来...
木叶七味居
传闻,从木叶建村之初,就有这样一家料理店。从凌晨开始营业,直到天亮之时关门。香味弥漫在小小的空间之中,令人沉醉。人们称呼这里为,七味居。...
我在末世有个鱼塘
末日里,他们都叫我神农,我有些名气,爷爷给我留下一座山和一片鱼塘作为遗产,我在后山的血尸地里养血尸卖血灵芝,把血尸当做饲料在鱼塘养鲨鱼。我赚的盆满钵满不愁吃喝。但是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没有人知道,...
农门悍妻:我娘子超凶
末世来临,路人甲莫雪同志不幸炮灰成了一只低阶丧尸。变成丧尸莫雪也不气馁,打架,咬人,卖力的吞噬血肉堪堪升为丧尸小头目,谁知又天降巨炮将她轰成了渣。本以为这辈子是凉凉了,谁知她竟然穿越到大晋朝成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