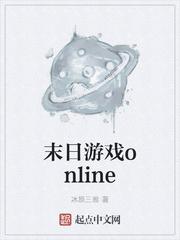第94章 第 94 章(第1页)
紫禁城的夜,柔软得像块发亮的黑绸子,蜿蜒的银河缓缓流淌,星辉下殿宇连绵,庄严肃穆。
待午门前的汉白玉日晷落下第一道日影,毓坤照例早起。
歇了一夜,虽身子仍有不适,精神倒比起昨日好了不少。
今日该是她去后宫给薛贵妃问安的日子,距辰时尚早,用过早膳,毓坤换了常服,带着冯贞向储秀宫去。
前些时日颇有些不顺遂,她不愿与薛贵妃添烦恼,有意将与蓝轩的不愉快瞒着她,但想必多少已有些言语传到了去,昨日终于等到旨意,毓坤心下一片轻松,自然要第一时间将这消息报与母亲,好叫她安心。
过隆宗门,在西二长街前下轿,毓坤抬眼便望见红墙黄瓦后储秀宫高扬的单檐歇山顶。
其下斗拱绘着苏式彩画,庭中古柏森森,汉白玉石基上东西各有一只铜鹿。
这里是她六岁前居住的地方,西面那只鹿她还曾骑在上面玩耍。
望见熟悉之景,毓坤的步伐不由轻快。
深红朱门迁延而开,毓坤但见石阶下候着一对丫鬟,皆衣罗绮珠翠,不似下人,倒像大户人家的小姐。
她心中明白,大约是薛府的两位夫人来了。
当年她受册为太子,连带外祖家也封了侯,因薛老太爷,薛大爷皆不在了,这爵位就由薛家长房长子,她的大表兄薛怀瑾袭了去。
虽是虚封,没有食邑,但延绵下的恩泽赏赐却是几辈子都受用不完。
所以不止在苏州老家,即便是在贵胄云集的京城,薛府的奢侈铺排,也是数得上名儿的。
宫人见太子驾临皆惊惶,毓坤却抬手,将向内通传的人止了。
她向来不喜薛府的招摇,又知道两位舅娘无事不登三宝殿,便立在廊上听了会,果然听到正厅中竟隐隐传来哭声。
薛家长房的蔡夫人以帕掩唇,泣道“可怜我瑾哥儿,让人打成这般摸样,三天尚下不得床,堂堂保昌侯府,竟叫人欺辱到这步田地”
越说越伤心,她哽咽得喘不上气来,薛贵妃叹道“人放出来就好,皮肉之伤,将养两日也就好了。”
蔡氏却如护崽的母虎,腾得起身道“话岂是这样说,如今娘娘是贵妃,位同副后,坤哥儿是太子,正是储君。
我们家是什么身份,那人又是什么身份,区区一个应考的举子,竟将瑾哥儿打了,那不开眼的巡城御史还将人拿了,可怜我儿在大狱中过了一夜。
好在顺天府尹识趣,弄清身份将人放了,只是若不将那打人者治个重罪,如何消得下这口气”
毓坤心知,若真如蔡氏所说,薛怀瑾无故挨了打,又怎会被巡城御史拿去,只怕是他先动的手。
因瞧在她的面上,顺天府尹不得已将人放了,本已是占了便宜,然她这舅娘不知足,还要编排颠倒黑白的说辞,想要将对方治罪。
见毓坤沉着面孔,身边宫人皆不敢喘气。
厅中的薛贵妃自然也是明白的,见蔡氏不肯罢休,冷淡道“这样的话嫂嫂莫再提,我虽入天家,却不过是做妾罢了,又有何贵呢,自己生的哥儿,尚不得唤一声娘,又哪有什么光彩可以荫护娘家。”
这一番话堵得蔡氏面上红一阵白一阵,讪讪道“怎可这么说话,皇上对娘娘可是”
薛贵妃打断道“瑾哥儿既从狱里放出来了,就在家好生养着,过几日改了纨绔习气,再捐个官儿与他做。
对方想必亦有伤,需好好赔偿,若是让人告到都察院去,只怕我也护不住。
还有便是,今日我既将这事了断,便不许再去烦扰太子。”
见她是铁了心不护短,蔡氏委屈极了,却不能不应。
一旁二房的郑夫人有些坐不住,试探道“这样一来,怕是要一笔花销呐。”
因长房袭爵,郑氏心中未免不平。
蔡氏守寡,有些事不好出面,她便在薛府掌家,一想到明明是长房惹了事,银子倒要打官中出,颇有些不满,却不便表现,只柔柔道“这些年替娘娘园子,也贴了不少钱进去,只怕公账上有些吃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