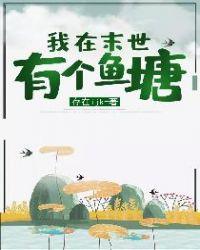第100章(第2页)
水绵软而多情,抚慰着我又累又冷的身体,身体一活泛,脑子便空了,我靠着浴缸臂不知不觉睡去。
是被锦年推醒,蒸汽氤氲中,她眼睛雪亮,双颊潮红,头发湿湿地贴在额上,脸上挂着一幅成色复杂的表情,似嗔怪似担忧也似尴尬。
“被你吓死了,怎么睡了呢?”
触着我似笑非笑的目光,她触电一样局促地扭开,声音低低的,“水都凉了,更容易感冒。”
她开水龙头,往浴缸里注热水,神情凝重地盯着热水气,只是不看我。
放差不多了,她站起来,指指浴巾,“快起来,好好睡去。”
边说边急急退出,偏巧地上有水渍,她走得太仓皇,脚底一滑,就摔了一跤。
我的笑便肆无忌惮地爆发,我说:“要不要我起来扶你一下?”
她又羞又气,狼狈无比。
我洗完出来,觉得头重脚轻,走路晃悠悠的,如踩棉絮。
“没事吧?”
她过来扶住我。
“没事才怪,”
我连连打着喷嚏,“我淋了差不多五个小时的雨。
你干嘛一声不响就走?你明知我一定会找到你。”
“觉明。”
她哀哀地看了我一眼,好像很无奈很可怜。
我最受不了这种目光,又加之思念心切,将她搂到怀里,抚着她毛茸茸的发,说,“锦年,对不起,这半年,公司特别忙,一直走不开。”
“我……”
她估计想说,“我没等你”
或者“我不要你来找我”
看我走了那么多路,淋了那么多雨,没法将这绝情的话说出来,只说,“快去休息,我找药去。”
锦年的卧室在阁楼,单人床,写字桌,衣柜,小沙发,简单到不能再简单。
但是小房间看上去非常温暖,只因桌上、床头鲜花葱茏,灼灼的色彩将灰暗的房子点缀得缤纷起来。
锦年喂了我吃药,我身体无力,头沉得像石块一样,暂时没有心思诉别情,挨着枕头便睡去。
不知多久,被手机铃音吵醒。
床头有暗黄的台灯,发着暖暖的光。
锦年站在光晕中,举着我的手机,“要接吗?”
我接了,是慕尼黑的同事向我汇报谈判进程。
我们正与欧洲一家企业谈战略合作,想在某些特定产品领域进行技术互补,以共度金融危机的冬天。
可对方似乎只希望获得我们的钱过冬,技术上还固守着堡垒,并不愿与我们平起平坐地置换,我们又不甘心只做一个小股东,所以谈判很难推动。
我在电话里做了些原则上的部署,费时三十分钟,艰难地结束谈话。
锦年已把食物端上来了,菠菜馅的意大利饺子,米粥,腌肉,还有色拉。
看上去香碰碰的,可是我并没有食欲。


![[清穿]四爷替我去宫斗](/img/1334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