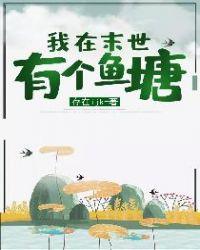我怎么当上了皇帝
身怀神捕系统,穿越高武世界,成了一个小小捕头。只不过,陆乾当捕头只想抓贼升级武功,在这危险的高武世界自保,顺便惩奸除恶,怎么当着当着就当到皇宫里头去了...
高武:从觉醒妖王血脉开始
科技与修真的浪潮里,谁能触及超凡?秩序与战乱的夹缝中,又是谁在低语?我看见妖族隐匿于霓虹之后,机甲飞跃在繁华街头王侯与邪魔推杯,众生和鬼怪换盏。当野心失去原则,科武制造毁灭,超凡带来罪孽,大厦将倾永夜降临,谁愿意做扑火的飞蛾?身负妖王基因而不自知的苏安,在十八岁生日那天原力觉醒,从此在充满血火与财富的都市开启了他的崛起之路。如果文明注定消亡,比起做飞蛾,他更愿意在敌人的尸体上建立一个新的世界!...
一品神卜
大师,我姓江,我老婆姓包,能不能给我儿子取个让人一下子就记住的名字?张楚江浙沪包邮!大师,我老公修电灯,睡厨房两天了,不起来,怎么办?张楚这是好事啊,可以吃席了。大师,我一个月赚三万,都给我老婆了,我爸爸生病,她不给我一分钱,怎么办?张楚你没拳头吗?大师,我今年四十二了,还是处女,我家世优秀,就想找个月薪五万,有车有房,不是二婚的男人,我不将就,就这么难吗?张楚女士,许愿请去庙里,我是相师,但我不是菩萨。张楚,一个不太正经的相师,天下第一魔女尚玄月的徒弟,因为魔女师父被人追杀,山门被炸,张楚下山,来到都市。颤抖吧,凡人!...
我在末世有个鱼塘
末日里,他们都叫我神农,我有些名气,爷爷给我留下一座山和一片鱼塘作为遗产,我在后山的血尸地里养血尸卖血灵芝,把血尸当做饲料在鱼塘养鲨鱼。我赚的盆满钵满不愁吃喝。但是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没有人知道,...
重生八零甜如蜜
曾经,你们毁了我的人生。现在,我回来了洗干净脖子,等我喂,那个谁,我不需要帮手,麻烦你离我远点儿行吗...
总管原名格蕾丝
1842年的一个春天,格蕾丝苏醒于贫穷的伦敦东区。在现代社会生活的二十几年,与在摄政时期生活的十几年,仿佛庄周梦蝶,让人难辨现实与虚幻。此时此刻,格蕾丝身处困境。母亲刚刚生下一对双胞胎,身体虚弱,父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