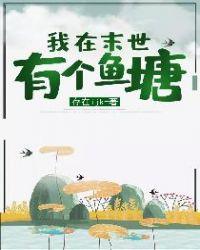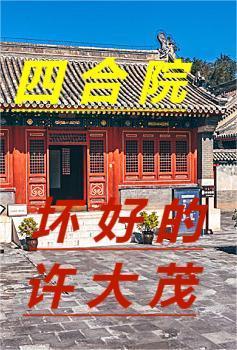第32章(第1页)
一时间,会客厅里的众人皆是瞠目结舌。
虽然雀儿并没有将那些既污秽又悲绝的画面说得有多详细,但只是三言两语,却也把钟仁暗中坑害老三,来满足其变态私欲的过往都说了个清清楚楚。
谁也想象不到一个大宅门里的家生子,一个正值青春妙龄的俏丫头,竟然会疯魔至此,完全不顾主子的体面和自己完全可以预料的下场,真的将那些隐在金玉之下的肮脏之事说了出来。
只不过,虽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哪个豪门大户的龌龊之事都不会少,但是像钟家大少这样变态到连亲兄弟都不放过的,却真是实属罕见了。
二房三房此刻像是挖到了什么天大的宝贝,从两房太太到小姐少爷,无不暗递眼色,窃窃私语,各人的脸上,只差没直接写上“幸灾乐祸”
四个大字。
何意如又如何不出她们的窃喜,只是这会子,她已是强自支撑,若不是身后椅子撑着,几乎便要瘫倒在地上。
她一生在后宅斗智斗勇,见过多少大风大浪,却未曾想今天会栽在一个丫头的手上。
以她的阅历和经验,却实在没有料到,雀儿竟会在如此大庭广众之下,彻底撕掉了自己和大房最后的脸皮。
按说以雀儿的聪明和心计,自是知道有些重要的东西,只有悄悄放在手掌心里,才能和人讨价还价,变成对她最有用的筹码。
而像现在这样把大房最隐晦、最肮脏的机密直接端出来,却绝计讨不到任何好处。
她这个样子,倒有些破罐子破摔的架势。
可是何意如又怎会忍她,大房的罐子就算再破,也是要高摆在其他两房的前面,又怎能任一个丫头说砸就砸。
何意如心下暗暗思量,眼睛便悄悄向一边的族长钟九,却见他面色沉郁,一边捻着胡须,一边却有些担忧地着老三钟礼。
何意如着他的侧脸,又了一眼钟礼的侧脸,心中长长地叹了口气。
钟礼从雀儿说完这番话后,便一直怔怔地站在那里,脸上的血色褪了又褪,几如白纸。
半晌,他终是开了口来,声音已有些沙哑。
“你说我和斑儿做了那事后,她便怀了我的骨肉,那她后来怎么又会得了那脏病,却是为何”
雀儿一只手抚着辫梢,一只手轻轻理了理胸口。
“三少爷一定要知道这些,便不怕心里难过吗也罢,既然已经说到这个份儿上,我便也干脆说个痛快,让你知道为何我一提起她,便要把贱人挂在嘴边了。”
钟礼狠狠地咬着牙根儿,从牙缝里逼出两个字来,“你说。”
雀儿的眼角向上轻轻吊起,“说来这便是大爷和大爷那迷药的功劳了。
自你和她那夜疯狂之后,不知是斑儿服食药物过多还是怎么,竟像是迷失了心性。
一天天活也不做,话也不说,连饥饱寒暖都不自知。
便是肚子里已经有了你的骨肉,一天到晚,还只拿一双骚眼睛盯着男人,倒将宅子里的爷们儿勾了个遍”
雀儿还欲还再说,钟礼却忽然伸出手,“行了,不用再说了”
秦淮到,有两行泪水,已经从钟礼的眼睛里滚落下来。
雀儿怔了怔,放下手里的辫梢,从怀里掏了掏,取出一方半新不旧,却洗得干干净净的手帕来,“三少爷,有一句话,我是一定要说的。
我之所以会这么恨她,便是因为她当年一心想要去你的房里服侍,却因见大爷不放她出去,便千方百计使了法子,让大爷把我从太太房里要了来,想要顶她的位。
若非如此,我又怎能进了泊春苑这个鬼窟般的地方好了,好了,擦擦眼泪吧三少爷,这么大的人了,竟还是会和小孩子时在太太房里撒娇一样。”
钟礼瞧都不瞧她一眼,任脸上的泪水不停地流着。
雀儿的声音这会子竟变得异样的温柔,“你瞧一眼这方手帕,可还认得吗这原是你在泊春苑下棋时,落在房里,却被我拾了来,洗得干干净净、熨得平平整整的。
唉,我也知道,手帕子再旧,因为你用过,我便觉得是天下难得的珍宝。